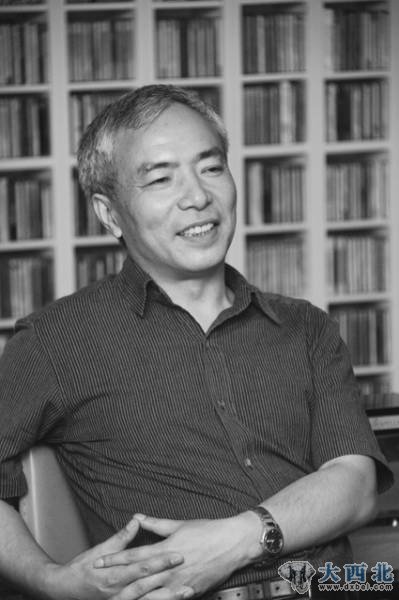
格非
格非说他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时,每天清晨都在作曲家爱德华·格里格的《晨曲》中醒来,那是学校的叫早音乐。从那时起,格非开始接触古典音乐,并成为一个发烧友,“因为音乐是这个世界能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”。
最近,这位在人们谈起中国的先锋小说时不可回避的作家,终于拿出他的新作《隐身衣》,实现了其多年前的愿望:把对音乐的感悟和热爱,写进小说里。格非将古典音乐包裹在“隐形衣”下,用音乐的样态,反观这个世界。
曾经不管不顾
“永远思考写作会让人疲劳。我的原则是想写才写,写完一部,休息一两年才会再写。”格非甚至会花时间忘掉写作这件事,恢复普通人的生活。在他看来,这才是最好的创作准备。
《隐身衣》是个特例。格非完成长篇小说《春尽江南》后,诗人北岛向他约稿,他本想推辞,却被拒绝。多亏北岛“不讲道理”地催稿,让格非仅用两个月时间便完成了《隐身衣》。
格非试图用音乐去诠释物质化及音乐与人的关系。这一点从小说每一章节的名字中就可凸显:KT88,《培尔·金特》,奶妈碟,莲12……都是音乐器材名称,或是古典音乐的乐曲名。格非并不担心与读者产生“隔阂”:“它们可堆积出音乐外化的、物质性的东西。中国古典音乐发烧友的数量之大堪称惊人,他们听到KT88等名词会很激动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也想同这些发烧友有交流。”
作为先锋小说作家,格非曾写过许多“不管不顾”的作品。如,1986年发表的处女作《追忆乌攸先生》。“写它完全没想到会发表。在意识形态严格限制下,我们通常会写两种类型的作品——一种是内容与社会重大主题有关联的,还有一种是打定主意不准备发表的。但没想到中国社会发展那么快、那么宽容。”
此后,他的许多“异类”作品被发表,并迅速受到关注。当然,格非并非不顾及读者感受。在写作过程中,他常将自己“分裂”成读者和作者双重身份,去审视自己的作品。
作家阅读要广、多、杂
格非的写作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,但他不是唯一的。
在1980年代,很多人都受现代主义的影响。现代主义是个很笼统的概念,其实具体说来有很多流派。当时,现代主义作品被大量翻译,作为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某种补充和反叛。格非恰好赶上了那样一个时代。“年轻人特别喜欢新的东西,喜欢挑战一种艰深的表达方式,所以很自然地与现实主义一拍即合。”
“老师认为大家要看托尔斯泰、雨果,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进不了教科书,也没人会介绍给你。”格非和朋友们在大量阅读现代主义作品后发现,其历史只有100多年,不可能涵盖整个文学史,便觉得自己非常“幼稚”,转而阅读古典作品或近代作品,那时他30岁。
宽泛的阅读面成就了格非。所以,格非也提醒年轻作家,若想做一个真正的作家,阅读一定要广、多、杂。
“年轻时只要有才华,即使准备不够,胆子够大,写一些别出心裁、别开生面的东西是可以的,问题是,你是否想一辈子当作家?如果只是玩票,那靠经历、勇气,也可以写出好作品。但如果要一辈子从事创作,恐怕就要懂历史,要有修养,需要很多积淀。”
格非以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举例:“很多人喜欢读村上春树的《挪威的森林》,却未必知道‘挪威的森林’的典故。其实,村上春树的修养非常好,知识面很广。”“有人只是学村上春树的调调,实在可怜。”
别将任何年代理想化
从江苏农村走出的格非,有自己的特质。“我喜欢寂寞。”他说,有次他一个人走在外面,突降大雨,雨从下午两三点一直下到晚上。“我撑着一把破伞蹲在野地里,我感到特别寂寞,那种寂寞现在想起来很伤感,但也确实很美。”格非还喜欢少年时代在村子里的自由、放任的生活。他当然也向往城市:“那时候,在县城看到汽车都能兴奋好几天,甚至认为汽油味是世界上最好闻的味道。”在他看来,那个味道就是文明,特别神秘。
从乡村到县城再到城市,格非说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基本吻合的——“我们从散漫的农村出来,经历上世纪80年代那样一个节奏缓慢的时代,到今天进入超繁忙、高节奏的时代;而人类社会,也是从百无聊赖到走进工业文明,再走到这个‘时间被切割得一塌糊涂’的时代的。”
在许多人看来,1980年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,但格非说:“当我们在怀旧的时候,很容易将记忆美化。不能把1980年代理想化,它有它的问题。”格非不“吹捧”那个年代。
“比如,那时,很多东西还是被禁止的,信息量没现在这么大,文化管理制度非常严格,作家随时都要说假话,不然出版不了。”格非反问,我们怎么能把那个年代理想化?
当然,格非也并不否认那个年代的美好:有理想主义色彩,大家嗜书如命。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,用格非的话说,“我们在一起不谈文学谈什么呢”?
“我觉得最美的就是晚上12点以后,整个校园非常沉静,所有人都睡觉了。我跟马原、余华经常半夜沿着河边散步,河上飘着一层轻雾。所以就像李叔同讲的,‘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生好时节’。”
格非仍然怀念那些在午夜、在河边谈文学的日子。
(责任编辑:陈冬梅)









